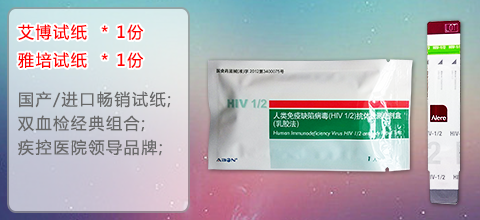艾滋病与道德审判
艾滋病公益检测网2013-01-11
恐惧、误解与道德化是艾滋病"污名"的主要根源。作为不断建构的文化和社会结果,"污名"和对"污名"的恐惧,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,比病毒本身更可怕。
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(UNAIDS)1月4日推出了《艾滋病相关用词使用指南》,供所有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员使用,其中不仅汇总了一些重要关键词的中英文对照,而且对一些不当用法进行了纠正。艾滋病署表示,通过恰当使用语言,可以加强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作用。推出这个指南的背景是,在对艾滋病防治的社会讨论中,“歧视”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艾滋病仍然是目前世界上对健康威胁最严重的疾病之一。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资料显示,2011年,约有340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。其中,67%的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,每20位成年人中几乎就有1人携带艾滋病毒。
2011年,艾滋病署发布了《实现“零”战略目标2011-2015年战略》,其中,将实现“零歧视”与“零新发感染”、“零相关死亡”并列,作为三大政策愿景和目标。战略指出,实现“零歧视”就是要去终止艾滋病相关的污名、歧视,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人们不愿意寻求预防、治疗、关怀和支持服务,从而使人群面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,增加了脆弱性。尤其是艾滋病“污名”,是防治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壁垒。
在社会学语境下,“歧视”(discrimination)和“污名”(stigma)作为语义不同的两个词汇而存在,代表了两种不同形式、却有因果关联的“偏见”或“不公正”的区别对待。一言以蔽之,“歧视”是已经付诸行动的偏见,而“污名”则更多代表了一种心理上的羞辱,赋予一类群体不受欢迎或耻辱的属性,使他们的个人地位在社会眼中受到严重贬低,进而可能采取行动上的排斥和孤立。“污名”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更广泛、危害同样深刻的“歧视”,在近几年才开始引起了较为热烈的讨论。
“污名”与心理上感受的“肮脏”似乎密不可分,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被烙上“污名”之后,“艾滋病人”已不再是一类疾病的受害者,而成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“社会标签”。透过这类标签,你似乎可以读到这样的强烈讯息:他们与正常人不同,身体枯槁、皮肤病变、记忆衰退,艾滋病晚期并发机会性感染和抗逆转病毒药物的不良反应,导致了生理上的缺陷和畸形;他们是静脉吸毒患者、街头的性工作者,或是男同性恋者,是毒品和“性道德”沦丧的“牺牲品”,因为叛逆、异常等个人品质上的“不良行为”和“污点”,而“获得了应有的惩罚”;他们可能是来自艾滋病高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,在世界广泛传播着“死神到来”的信号。尽管对因为母婴传播而感染艾滋的孩子,或者那些通过献血途径而感染艾滋的病人,社会公众大多持同情的态度,但对待前者刻板、消极的印象,并没有得到撼动。潜台词就是提醒大家:“快避开”、“隔离你”或是“驱逐他”。
“污名化”不仅停留在艾滋病感染者单纯遭受到的心理歧视,会进一步发酵、酝酿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和过程:首先是直接歧视,表现为承受污名的人被周围的人贬低、躲避、隔离,或是被拒绝和被剥夺各种机会,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。可能是被施加言语诽谤、被拒绝就医、被隔离到专门的医院才能就诊,或是被工作单位的上司和同事裁员或拒绝录用,乃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。其次是结构性歧视,因为他们道德上的“污点”和“不良行为”被看作是“自作自受”,不再被赋予“同情心”,获得的关心和援助也比其他患者来得更少。艾滋病感染者不仅感受到社会公众对自身的负面态度,心灵受到不可愈合的创伤,而且他们会将这种负面认知和羞辱内化,降低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,从而造成隐瞒得病真相、拒绝就医、将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逼入地下,加剧了艾滋病传播和扩散的可能,构成了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。除了社会上“原发性”的污名歧视,来自家人承受社会压力后而产生的“继发性”污名歧视,也往往成为压垮艾滋病人心理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,迫使他们产生抑郁、自杀乃至反抗社会等消极的举动。
恐惧、误解与道德化是艾滋病“污名”的主要根源。作为不断建构的文化和社会结果,“污名”和对“污名”的恐惧,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,比病毒本身更可怕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把“个人行为是否存在污点”凌驾于疾病之上,对患者进行“道德”的审判和惩罚,那么看似伸张了社会正义、张扬了道德力量的背面,必然是放大了被“污名化”和“妖魔化”的不良行为和一群等待接受社会惩罚和道德拯救的“犯人”。
然而,艾滋病作为一种“疾病”存在,而非违反社会道德和法律的“犯罪行为”,“治病”才能“救人”,爱心与关怀本身比什么来得都重要。我们不仅要去“还其清白”,归还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应得的尊重和公正的对待,更多需要做的是,怎么去治疗公众心里被放大了的恐惧和似乎摆脱不了的“洁癖”。
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(UNAIDS)1月4日推出了《艾滋病相关用词使用指南》,供所有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员使用,其中不仅汇总了一些重要关键词的中英文对照,而且对一些不当用法进行了纠正。艾滋病署表示,通过恰当使用语言,可以加强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作用。推出这个指南的背景是,在对艾滋病防治的社会讨论中,“歧视”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艾滋病仍然是目前世界上对健康威胁最严重的疾病之一。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资料显示,2011年,约有340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。其中,67%的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,每20位成年人中几乎就有1人携带艾滋病毒。
2011年,艾滋病署发布了《实现“零”战略目标2011-2015年战略》,其中,将实现“零歧视”与“零新发感染”、“零相关死亡”并列,作为三大政策愿景和目标。战略指出,实现“零歧视”就是要去终止艾滋病相关的污名、歧视,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人们不愿意寻求预防、治疗、关怀和支持服务,从而使人群面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,增加了脆弱性。尤其是艾滋病“污名”,是防治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壁垒。
在社会学语境下,“歧视”(discrimination)和“污名”(stigma)作为语义不同的两个词汇而存在,代表了两种不同形式、却有因果关联的“偏见”或“不公正”的区别对待。一言以蔽之,“歧视”是已经付诸行动的偏见,而“污名”则更多代表了一种心理上的羞辱,赋予一类群体不受欢迎或耻辱的属性,使他们的个人地位在社会眼中受到严重贬低,进而可能采取行动上的排斥和孤立。“污名”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更广泛、危害同样深刻的“歧视”,在近几年才开始引起了较为热烈的讨论。
“污名”与心理上感受的“肮脏”似乎密不可分,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被烙上“污名”之后,“艾滋病人”已不再是一类疾病的受害者,而成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“社会标签”。透过这类标签,你似乎可以读到这样的强烈讯息:他们与正常人不同,身体枯槁、皮肤病变、记忆衰退,艾滋病晚期并发机会性感染和抗逆转病毒药物的不良反应,导致了生理上的缺陷和畸形;他们是静脉吸毒患者、街头的性工作者,或是男同性恋者,是毒品和“性道德”沦丧的“牺牲品”,因为叛逆、异常等个人品质上的“不良行为”和“污点”,而“获得了应有的惩罚”;他们可能是来自艾滋病高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,在世界广泛传播着“死神到来”的信号。尽管对因为母婴传播而感染艾滋的孩子,或者那些通过献血途径而感染艾滋的病人,社会公众大多持同情的态度,但对待前者刻板、消极的印象,并没有得到撼动。潜台词就是提醒大家:“快避开”、“隔离你”或是“驱逐他”。
“污名化”不仅停留在艾滋病感染者单纯遭受到的心理歧视,会进一步发酵、酝酿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和过程:首先是直接歧视,表现为承受污名的人被周围的人贬低、躲避、隔离,或是被拒绝和被剥夺各种机会,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。可能是被施加言语诽谤、被拒绝就医、被隔离到专门的医院才能就诊,或是被工作单位的上司和同事裁员或拒绝录用,乃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。其次是结构性歧视,因为他们道德上的“污点”和“不良行为”被看作是“自作自受”,不再被赋予“同情心”,获得的关心和援助也比其他患者来得更少。艾滋病感染者不仅感受到社会公众对自身的负面态度,心灵受到不可愈合的创伤,而且他们会将这种负面认知和羞辱内化,降低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,从而造成隐瞒得病真相、拒绝就医、将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逼入地下,加剧了艾滋病传播和扩散的可能,构成了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。除了社会上“原发性”的污名歧视,来自家人承受社会压力后而产生的“继发性”污名歧视,也往往成为压垮艾滋病人心理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,迫使他们产生抑郁、自杀乃至反抗社会等消极的举动。
恐惧、误解与道德化是艾滋病“污名”的主要根源。作为不断建构的文化和社会结果,“污名”和对“污名”的恐惧,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,比病毒本身更可怕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把“个人行为是否存在污点”凌驾于疾病之上,对患者进行“道德”的审判和惩罚,那么看似伸张了社会正义、张扬了道德力量的背面,必然是放大了被“污名化”和“妖魔化”的不良行为和一群等待接受社会惩罚和道德拯救的“犯人”。
然而,艾滋病作为一种“疾病”存在,而非违反社会道德和法律的“犯罪行为”,“治病”才能“救人”,爱心与关怀本身比什么来得都重要。我们不仅要去“还其清白”,归还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应得的尊重和公正的对待,更多需要做的是,怎么去治疗公众心里被放大了的恐惧和似乎摆脱不了的“洁癖”。